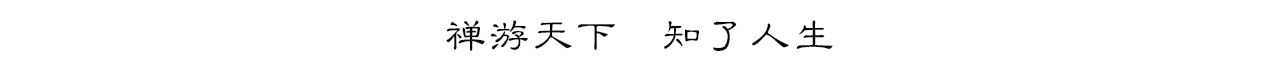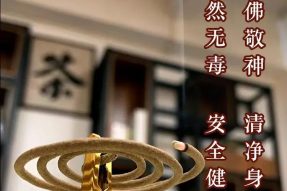佛寺:从印度到南亚和汉地的演变
佛教寺庙,构成了一种独有的建筑空间,象征了一种特殊的宗教意义。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是由起源地印度向南(东南亚)、北(中亚、东亚)、中(西藏)外传而形成,佛教建筑,随着佛教的外传而充满佛教圈中的地理空间。这里面有着很多的宗教、哲学、文化课题。本文着重从佛寺的角度谈佛教建筑从印度到南亚和中国的演变,并在这一演变中探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传播与接受中产生的建筑形式变化。从佛教文化圈的大角度看,佛教寺庙,作为与佛教石窟相对应的地上空间结构,更主要的是,作为佛教的一种重要建筑形式和意义象征,是在印度之外,即在南亚、汉佛圈和藏佛圈中形成的。本来,塔、窟、庙就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发展可能,然而,这种可能在印度本土未能充分展开,在南亚,虽也遍布寺庙,但不仅寺主要是塔寺,更重要的是,作为建筑,寺远不如一系列名塔那样英名远扬,因此,寺庙,作为佛教境界,在汉佛圈和藏佛圈显出了自己特有的光彩、迷人的魅力,蕴含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历史、哲学内容。本文主要讨论印度、南亚佛教建筑与汉佛建筑,先从印度讲起。
印度佛境,主要是由两种建筑形式来体现的:塔与石窟。这并不是说印度没有佛教寺庙,而是在于,(1 )印度的佛寺没有超出石窟的境界;(2)在相同的空间结构中,石窟更能体现出印佛的独特追求, 正象印度文化的另一主流印度教的寺庙最能代表印度教的特殊风采一样;(3)印度佛寺,在演化逻辑上, 处于从印度石窟向南亚塔寺演化的中间项段,还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定位。因此,省去佛寺,仅从塔与石窟的关系来看印度佛境,更能显出佛教在印度与整个文化的有趣关系。佛教在阿育王时代被政治权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力提倡和普遍推行,产生的是塔的遍地出现。但是僧侣主流却没有与塔一道进入社会中心的公共空间,而依然退隐山崖。作为被王权推崇为全社会敬仰的具有文化意识形态象征意义的塔,是矗立蓝天之下面对广大公众的塔。作为修道的极至境界、僧侣的沉思对象的塔,是少人的山崖边、静寂的石窟中的塔。也可这样说,塔是不住僧人的塔,石窟是要住僧人的塔。拥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公共中心的塔与仅有宗教虔诚和个人修道的石窟构成了印度佛教的二重境观。一方面,可以说,印度佛教的建筑象征就是塔,因为石窟的中心也是塔。另方面,石窟又不同于塔,塔主要是一种社会的公共空间,石窟主要是一种远离社会的宗教空间。政治与佛教、王权与僧侣,有着不相同的一面,佛教的外传,并没有变成印度政治的外传,僧人的传教并非都与印度的王权相关。因此塔与石窟却又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二者共同构筑了印度的佛境。
印度本土,塔与石窟的两种境界在于僧人与政治在趣旨上的分离,仅就这种趣旨的分离而言,塔代表了佛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石窟体现了佛与僧侣的关系,更主要的是,石窟体现了一种印度僧侣的远离社会和政治的“隐”的志趣。一旦僧侣主流要走进社会,佛教建筑上的石窟主潮就变成了寺庙主潮。就建筑的内部空间而言,石窟与寺庙是一样的,从这一角度看,石窟是山崖的、远离市俗的寺庙,寺庙是地上的、进入社会的石窟。因此,石窟主潮还是寺庙主潮,折射着一种文化/历史/观念的逻辑关系。佛境三相塔、窟、庙相互关联,正象窟与庙一样,塔与庙同样有一种转换关系。塔是无僧侣居住的公共建筑,但它又是佛教的建筑体现,一旦僧侣要进住塔中,塔为了容纳僧侣的进入而变成了寺。因此,塔、窟、庙体现的是僧侣与社会文化的三种特定关系。
塔、窟、庙三者的逻辑关系已经预含了寺庙主潮出现的可能。然而,在印度本土,政治与佛教结合和僧侣与政治的疏离所构成的佛教塔与窟的二重境界一直是印度佛教艺术的主流。塔和窟向庙的逻辑进展,对佛教来说刚刚显露头角,就被具体的历史语境所阻止。但如果不仅从佛教,而从整个印度文化史来说,塔与石窟向寺庙的演化又是按自身的规律进行的。印度文化中,塔为佛教的专有,石窟是佛教与印度教以及耆那教共有,接着石窟的低潮而出现的是印度教寺庙在地面上的大量出现。因此,塔、窟、庙在印度的演化呈出了建筑史与宗教史的复杂关系。(目前有案可稽的佛教寺庙,在结构上多与毗诃罗石窟相类,同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印度教寺庙形成鲜明的对比。四世纪的菩提拉耶寺是一座塔寺,但其建筑形式与佛塔不同,而与印度教的寺庙更为相似。在它上面反映出来的正是建筑史与宗教史的互渗和混杂。)对建筑史来说,塔、窟、庙是逻辑的有序演进,对佛教艺术史来说,是演进逻辑的无序性断裂。
不过,这种佛教艺术史在印度本土的断裂却在印度本土之外被结联上了,这就是佛教南、北、中三条外传路线上的佛寺的出现。不过,三大佛教圈各有自己的由塔、窟向寺庙的转化理路。南亚佛教以塔为主,因此庙由塔演变而来,这种演变的建筑逻辑在缅甸蒲甘表现得最为清楚。在这一演变理路中,由于庙是由塔而来,庙在建筑形式上仍然是一个塔,是塔的扩大,这里的扩大,不仅是建筑实体和建筑空间的扩大,更是功能的扩大,是僧侣进入塔而使塔成庙,它不仅是佛教建筑塔与公众的关系的重写,也是僧侣与社会关系的更新。不管蒲甘这种由塔变庙在南亚有多大的普遍性,但它确实象征南亚佛教与南亚政治/社会/文化的关联与印度本土是不一样的。正如塔在南亚有不同于印度的发展演化逻辑一样,南亚的由塔变庙象征了南亚佛教根据自身的本土文化特性对佛教的新创。
由塔变庙的逻辑,决定了由之演变而来的寺庙的建筑特征,不是平面的扩展铺开,而是立体的向高发展。这样,已经成为庙,但还具有塔的外形。从这一逻辑,可以更深地理解南亚佛塔向高大方向转变。南亚庙的向高发展与塔的演化完全一致,在于一个相同的文化机制,是一种机制中的两种新创。具有佛塔外观的寺庙,既成为了寺庙,又没有破坏南亚佛教的塔中心的权威,在用寺庙突出僧侣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以自己塔的外形继续了塔所象征的佛教与政治的关联,增加了塔原来没有的意义:僧侣与社会的关联。正象印度的塔与石窟构成印佛的二重境界一样,庙和塔呈现了南亚佛教的独特的文化趣旨。
从蒲甘佛庙可以看到,庙顶上是佛塔,庙里是佛像。由塔到塔像一体是印度石窟的演进逻辑。在南亚,由塔向塔像一体的演进呈出了两种方向,一是从塔自身的演进中出现塔中像和塔前像的塔像一体,二是从塔到庙的演进,在庙中出现庙顶塔、庙内像的塔像一体。在塔自身的演进中,塔像一体始终把像保持在塔,在庙的塔像一体中,塔和像是庙的整体中的两个部位。在这一意义上,庙对于塔和像又可以根据自己认为突出整体意义的最佳方式来进行建筑形式组合。塔在庙顶,宜于远观,不合近看,它形成的是庙中僧侣与塔间接的心灵关系而不是直接的视觉关系。如果把塔从殿顶放至殿前庙内,塔与僧侣就有一种直接的感觉拥有。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一体验,反正南亚佛庙,塔在庙顶的少,仅有尼泊尔的白观音庙和缅甸曼德勒山八寺中的塔庙等,而塔在庙院内的多,有缅甸阿难寺、柬埔寨乌那隆寺、泰国玛哈达寺等。这种数量关系当然有窟与庙的关联,印度寺庙与南亚寺庙的关系。在南亚特别表现为佛教的林居派与村居派的差别。但从由塔变庙这一条路看,可以把塔在庙顶看成是从塔到庙的过渡阶段,而塔在庙中,视为从塔到庙的完成类型。塔在庙中,宜于近绕,这是庙内的仪式功能;塔本高耸,也适于远观,满足公众的瞻仰。然而,无论塔是在庙顶、是在庙内,庙,在南亚的发展,一直保持着塔像一体的塔中心,正象石窟在印度的演变,没有超出塔像一体的塔中心一样。而这,既是印度与南亚同为以塔为象征意义中心的印度佛教圈的原因之所在,又使得南亚的佛教艺术完全可以以塔的演化作为代表。
与南亚佛教寺庙一直受制于塔不同,汉庙走上了超越塔中心的新路。汉庙出现后,塔逐渐失去了在庙中的中心地位,甚至被挤出庙外,成为庙的可有可无部分。但这种差异使汉庙呈出了不同于南亚庙的功能和境界。不从僧侣与建筑的关系看,只就建筑自身的结构讲,印度的山崖之窟和地上之寺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一定数量的支提结构和毗诃罗结构构成一个僧团的修道生活空间,而成熟的汉寺是把这两种不同功能建筑组织在寺庙的整体之中。汉佛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意义结构对寺庙的建造进行了不同的空间重g。
汉传佛教寺庙被称为“寺”,源于印佛东来在汉地出现的第一座佛教建筑被取名为“白马寺”。当时,“寺”并非宗教建筑之称,而是政府机构的官署之名。围绕白马寺,有种种传说,从建筑成分讲,它有殿、有塔、有画,依照的是“天竺旧状”,但用政府机构去命名,不仅是以一种在汉文化中尊贵含义的建筑概念去使佛庙一听上去就令人肃然起敬,更主要的是它在建筑形式上就接受了汉文化的礼制。白马寺的实物原样已无法可考,现在能看到的白马寺把主建筑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这使人明显地感到佛寺与皇宫布局上的相似,故宫的沿南北纵轴线是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干清宫,只是规模和气派更大。汉文化的建筑,本就是以皇宫为最高范本,各类建筑按照统一结构,在规模和尺度上遵从礼制而缩小。也就是说,汉文化的皇宫、官署、府第、民居,都是按照统一的礼制和观念来建造的,皇宫是最大最高级表现,四合院是最小最低型,都是坐北朝南,纵轴展开,左右对称,堂堂正正,尊卑分明,秩序井然。佛庙一开始,从名称到结构,都被结合进汉文化的建筑体系之中,正因为如此,在汉化佛庙史上,很多宫府不须大的改动就可以变为佛寺,北京雍和宫就是从明代内宫的监官房变为清代的亲王府再变为佛寺雍和宫,四川报恩寺也是初修王府,后为佛寺。这都是明清之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佛寺都是由捐出的府第住宅改造而成,基本方式是“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若是达官贵人的府第而成,也就“廊庑充溢,博敞弘丽,”“金花宝盖,遍满其中。”总之,佛寺之为寺,在汉文化建筑体系中属于贵的等级。
如果说,“寺”的起源与贵相连,揭示了佛寺在汉文化建筑体系中的高等级的一般特征,那么汉传佛教寺庙又称为“庙”,则显出了佛寺在高等级中的宗教性特征。庙,是供奉不同于人世而又与人世相关的祖宗之处,祖宗已属不同于人的神的世界,因此庙又是神的居所。佛从西来,也被看成是神之一种,因此佛寺为庙。佛寺的建筑自然而然地进入汉地庙的形制之中。汉文化的庙是依等级而来的,周代“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候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礼记·王制》)这时的七、五、三,是指的单体建筑中的多室。但之所以如此,在于庙本已为群体建筑“前宫后庙”、“明堂宗庙”中的一个部分,当宫与庙分开来之后,庙也就根据自己的等级和其它因素而成为独院式、二重、三重或多重院式的形制了。正如远古之时前宫后庙的“离离在宫,肃肃在庙”(《诗经·大雅·思齐》)的宫庙一体格局中,庙服从和服务于宫一样,在重现世的汉文化中,宫与庙虽然在小空间上已经分开,但在大空间上仍然一体,庙仍然是汉文化整个建筑体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仍然服从和服务于宫(皇权)。因此,汉文化之庙,无论是那一种庙,在建筑结构上都是相似的。看看北京白云观、广西恭城孔庙、浙江绍兴禹庙。与上面的佛寺比较一下,再与皇宫、府第、四合院对照一番,可知佛寺已是与汉文化建筑体系融为一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种坐南朝北,主要建筑放在中轴线上,构成时空合一的整体。以两边的建筑来突出中线上的主要建筑,从对称中显出庄严。中轴线的建筑以一种断连节奏和高低旋律展开,在内容丰富的时间行进中,突出一个中心:大雄宝殿。这一中心使整个寺庙形成等级秩序。建筑之间的空间既构成了时间和心理的运动,又在这种双重运动中使整个寺庙之中有一种汉文化的虚实相生的韵致。
佛教是信仰体系和智慧体系的合一,如果说在汉代,它的初来是与汉地的信仰体系结合,也就是被作为神仙、方士、道教一类接受,那么在魏晋南北朝,它的发展更进入与玄学思辩的应合。因此佛庙在汉地,是与两类建筑一道演进的,一类是士大夫的宅院,当东晋以来,士大夫的私人园林产生繁殖,连皇家建筑也受士大夫情趣的影响,佛寺也与整个社会风尚一道带上了园林风趣。当然也与士人与皇家一样,花园是次要,纵轴为主、左右对称的整严是主体。另一类,也是更重要的一类是道教建筑。如上面所引,在建筑结构上,道观与佛寺一样,但道教一方面为了吸引各界人士,造庙于闹市,另一方面为了修道成仙,又建观于名山。佛教入汉地,成为与道教的社会功能基本相同的宗教,同样是把自己的寺庙向这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建于城市以接近朝廷,一方面筑于山林以高尚佛心。这两方面,庙堂与山林,又正是汉文化士大夫的心理/价值/行为取向。印度佛教窟筑于山崖,呈出的是他们的苦行心性,汉地佛教建筑寺于山林,既承传了印佛的隐修之志,又深得汉文化的山林之趣。东晋慧远在庐山建东林寺,与玄学家、文人士大夫一道赏山观水,谈佛论玄,声名远扬。随汉佛的流传,汉地名山布满佛寺: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天台山、太白山、清凉山、梵净山……
山林佛寺并没有改变建筑的纵轴为主、左右对称的基本结构,这个结构是为保证和造就严肃心理必需的。但是寺在山林,自然要求建筑与山水环境的协调,山中佛寺,以整个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各寺的位置,这里佛寺的建筑与汉文化的山水理论和风水理论结合起来,山中各寺的位置,与山的形态气脉完美结合,显出整个山的精神。一寺之址,按风水的最佳四灵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模式使之“环若列屏,林泉清碧”,“宅幽而势阻,地廊而形藏”,如浙江的保国寺和天童寺。当然也因山的形态而可以有更多的通变,例如,寺门本应在寺的正中,普陀山法雨寺,寺门在寺东,但依风水理论,是“生气东旺”,按山水特点,是凭栏东望,可见“海天万里”,于是改在东面,并建高阁三间,以使入寺路口与整座寺庙合谐。按风水理论,门向就对着山的“气口”,依山水特点,门对着气口,才能望远,生苍茫无限之感。九华山拜经台寺四面环山,背倚天台峰,左是鹰峰,右为金龟峰,前对观因峰,只有观音峰与金龟峰之间有一条狭长谷口,即风水理论中的“气口”。限于地势,该寺无法正对谷口,于是寺门偏斜,朝向气口。寺内的建筑部件也因与汉文化的观念相结合而有了改变,天童寺前有两池叫“天池”,进寺之路两绕两池之中,呈斗形,池为天池,斗当然是北斗,于是在二池之间的路上建七塔,“两池象斗,七塔乃七星之象”。“七塔,四白三赤,白以生水,赤以厌火。”(《天童寺志》)
汉地佛庙在布局规整和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上进入了汉文化的建筑体系之中,只有这样,它才进入汉文化结构之中并进行正常运转和发挥功能。但佛寺之为佛寺,而不是道观、府宅,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建筑符号,即佛塔与佛像。寺中有塔,一望就知为佛寺,殿里有像,一见便晓为佛陀。但在塔与寺中,塔作为崇拜偶像的建筑形式,是外来的,像作为求拜偶像的雕塑形式,是本有的。印佛之庙(窟)本以塔为主,汉佛寺庙作为印佛寺庙的接受模仿者,最初是原样照搬,而后塔殿并重,但以塔为中心。再以后,佛殿因供奉佛像(这是汉文化最熟悉的崇拜方式),其地位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寺院的主体。而塔,这种非汉文化的崇拜方式,在寺院中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最后被请出寺门之外,成为求拜体系中可有可无的成份。正像整个佛教石窟的历史演变一样,汉地寺庙经历了由塔中心到塔像并重到殿中心的历史演化。从《阿弥行状记》中记载的隋唐以来各佛教宗派的建筑主要成分的排序,可以从塔在各派中的重要程度折射出塔在汉地佛寺中的衰落史:
法相宗寺院:佛殿、讲堂、山门、塔、左堂、右堂、浴室。
天台宗寺院:佛殿、讲堂、戒坛堂、文殊楼、法华堂、常行堂、塔。
华严宗寺院:佛殿、食堂、讲堂、左堂、右堂、后堂、塔。
密宗寺院:佛殿、讲堂、灌顶堂、大师堂、经堂、大塔、五重塔。
禅宗寺院:佛殿、法堂、禅堂、食堂、寝室、山门、厕所。
除了法相宗外,其他三派都把塔放在最后,而在禅宗寺院里,塔就消失了。
在汉佛寺庙里,建筑实体上从塔中心到殿中心的转移,以及与之相连的观念心理上从塔崇拜到像崇拜的演变是从印佛到汉佛的一个方面,而把佛像崇拜变成汉文化的偶像崇拜是佛寺汉化的另一个方面。佛寺偶像崇拜汉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殿内塑像的变化,二是寺庙中各部分的变化,以及寺院整体布局中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的变化,由于汉地佛寺主要是木建筑,唐以前的寺庙早已消失殆尽,因此从现存寺庙里无从寻找其演变踪迹,但敦煌从北朝以来的石窟塑像的变化,因石窟空间正好与地上寺庙的佛殿相当,从而恰巧提供了地上寺庙佛殿内塑像演变的脉络。从总的方向,可以推出,佛殿塑像的变化,是从一佛,至一佛二弟子,到佛、弟子、菩萨、罗汉、力士的演变。然而,从已存的佛殿看,演变的终端,更多地凝结为,北墙坛上是大佛,或三身,或五身,或七身,也可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三佛各带二胁侍菩萨,总之要用三、五、七等单数构成一个向心的中心结构。东西两壁前,多为十八罗汉,整个殿又构成一个等级的向心结构,这种结构正是金銮殿上的皇帝与群臣的等级结构,元帅府中元帅与众将的等级结构,衙门里的县太爷与听差打手的等级结构。石窟中为了照顾东西壁壁画的效果,把等级结构都集中到北壁坛龛上,佛殿里一般不突出壁画,两壁的塑像更显出秩序的严格肃整。然而,无论是石窟的定型,还是佛殿的定型,在本质上,都显出了佛的呈现方式从印度文化的个人方式到汉文化的等级排列方式的演变。皇帝的神圣,官吏的高大,都是从这种等级结构中显示出来的,法力无边的佛陀也要从这种等级结构中才让对他顶礼膜拜的人们产生确有法力的感受。
汉佛寺庙除了已讲的大雄宝殿,就是在中轴线上,进到大雄宝殿之前的山门和天王殿了。山门有三,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象征佛家的三门解脱,但门却是殿堂式,有汉地本土的尊贵。印度窟寺,门外是佛像,人们来要见的本就是佛,在汉地,佛为最高“神”,像皇城中的帝王。衙门中的太爷,不会随便就见,山门的殿堂里一边一个金刚力士,作为佛门圣地的护法门卫。金刚力士在印度只有一位,是法意太子,皈依佛法后成为佛的500执金刚的首领。但在汉地的等级秩序观念中, 一位没有视觉效果上的威严,就变成两位,与任何府第民宅的门神格式一样了。但新增的一位为谁,始终没有经典根据和圆通解释,还是后来《封神演义》自创新注,说是哼哈二将郑伦、陈奇死后封神之位。这种小说家言,一般民众会以此为求知的满足,严肃的僧人对之却难以苟同。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地佛寺的建筑结构和塑像的群体结构都确实需要有左右对称的两位门神。
走进山门,就是前殿,天王殿,有六尊塑像,殿中对着山门的是弥勒,两侧是四大天王,弥勒背后,由板壁隔开,面向大雄宝殿的,是韦驮。
四大天王与门神性质相同,只是地位更高。宇宙的中心是须弥山,四大天王的府第在须弥山腰的犍陀罗山的四座山峰上。须弥山四面是四大洲:东胜身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四大天王各管一洲,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四大天王由西域进入汉地,他们的容貌、装束、法宝、武器不断演变,功能、定位、甚至出身、姓名也变来变去。最后,汉寺四大天王,以《封神演义》的魔家四将为基础,综合整个佛教的四大天王史,定位为:增长天王魔礼青,掌青光宝剑一口,职风;广目天王魔礼红,掌玉碧琵琶一面,职调;多闻天王魔礼海,掌混元珠伞一把,职雨;持国天王魔礼寿,掌紫金龙花狐貂,职顺。东南西北,风调雨顺,真是对应了现世生活的需要,四大天王两边威武肃立,与弥勒菩萨正中洒脱笑意构成了一幅意味深长的汉化佛教景观。
弥勒后面的韦陀,这位或者挺直站立,双手合十,两腕横托宝杵,或者右手插腰,左手握杵拄地,英俊威风护法神,若要细考,来历不明,有i说是室健陀天的错译,他确是由唐代高僧的梦中而慢慢进入现实。在道宣的梦中,他自称是诸天之子,统领鬼神,而且是受佛陀所令,护持佛法。它能占有汉佛大庙中的一个重要位置,其演化理路在根本上与金刚和天王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汉佛寺庙所包含的一种巧妙的整体结构方式。他处于天王殿中,是天王殿的一部分,却面对大雄宝殿。他保卫的主要对象是佛,这座塑像本身就把人引向寺院的最高潮——佛陀所在的大雄宝殿,而从天王殿到大雄宝殿之间的空间都在他的视域之内。
天王殿的主角是弥勒。他在世时是菩萨。大乘佛教修行,成正果的等级有三:罗汉、菩萨、佛陀。弥勒处在第二级,但弥勒菩萨入灭时,释迦牟尼说,弥勒是他的继承人,在将来度尽众生时成佛,因此,弥勒是未来佛。弥勒,现在是菩萨未来是佛,作为天王殿的主像,就有内含丰富、可供想象的寓意,同时又构成与供佛的大雄宝殿在空间相连、时间相接的一个最恰当的递进点。有意思的是,近代佛寺天王殿中的弥勒菩萨往往是头体肥胖、肚皮特大、笑口大开的尊相。这是五代的布袋和尚契比,一生从形体到行为都充满欢乐的喜剧性。他在浙江奉化岳林寺东廊的磐石上圆寂之时,称自己是弥勒的化身:“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世人总不识。”天王殿上的大肚弥勒给人以人世的喜悦和人情的亲近。近代佛寺里关于弥勒的最有名的对联体现出来的更是浸透着世间情味的哲理: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诸事
天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接着就是寺庙的高潮,朝拜佛陀的圣地,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中的佛像结构,前面已经讲了。
这里讲的汉寺,是从汉文化的一方面,把佛作为宇宙的主宰、作为外在之神这一面来讲的。汉文化对佛还有另一种理解,把佛作为心灵的自由境界,这就是禅宗。风行的唐宋的禅宗寺庙是另一种境象,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上一篇: 布达拉宫
下一篇: 阿尔寨石窟—草原文化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