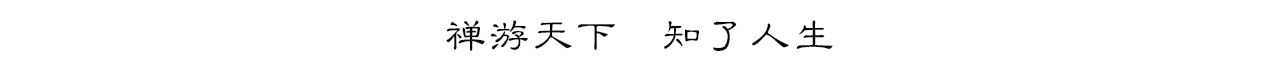佛教音乐对话
对话者:
田 青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佛教研究专家
凌海成居士 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学者
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
地点:北京潮音斋
田:你我认识有二十年了吧?
凌:今年整二十年。
田:咱们和佛教音乐结缘也二十年了!
凌:是啊,你是一心一意,大有建树;我是三心二意,一事无成。
田:随缘就好。我这辈子就庆幸自己可以一心一意干自己爱干的工作(指从事佛教音乐研究)。
凌:我也庆幸自己这辈子可以三心二意乱干自己爱干的事儿。说起佛教音乐,我在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的编委时,曾在佛教音乐部分写了一篇《北京智化寺音乐述略》。其间对智化寺音乐、佛教音乐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一些问题思考较多,有些问题佛教界和音乐界都很关注,意见也多有分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首先想请你谈谈什么是佛教音乐?你对我国佛教音乐的总体认识是什么?
田:什么是佛教音乐这个问题,要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认识。狭义的佛教音乐一般指佛寺中的殿堂唱诵,也就是正规称作“梵呗”的仪式音乐。有些不属正规仪式的应酬佛事音乐,因为核心仍然是佛教,也应属于此类。这一点大家争议不大,但广义佛教音乐的定义就很难下了。前年你我去台湾参加“中国佛教音乐研讨会”我在台北一家音像书店里看到有半间屋子那么多的佛教音乐磁带,名目真是不少。但仔细一看,大多是冠以佛教标题的民乐作品,如《鉴真东渡》等。还有的竟然敢把密宗的什么本尊硬按上做标题。我奇怪有些人对密宗全然不懂,对密宗的仪轨也一窍不通,怎么就能进行创作呢?这种东西也叫佛教音乐?我真不敢苟同!前几天,我领着加拿大温哥华大学一位音乐教授到寺院去听佛教音乐。这位教授告诉我,他会唱中国的佛曲。请他唱过,原来就是广为流传的《观音圣号》。他说是在香港、广东等地学的。圣号只一句,反反复复而已。这么一句圣号,算不算佛教音乐呢?是否有利修行,我不敢妄断。听了能不能开悟,就更不好说了。
凌:我对佛教音乐的认识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二十年前接触的佛教音乐主要是传统佛曲,例如殿堂唱诵、智化寺音乐等。那时,出于一个信众对佛陀的虔诚,便也把这些音乐视为佛经一样神圣,并且认为它们源于佛教。但后来随着对传统佛乐的了解加深,我才知道今天所能听到的那些古代流传下来的佛教音乐几乎全部从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移植过来。就连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创作的佛教歌曲也无一不是直接套用外国歌曲的旋律。这曾使我非常失望,因为这些被移植的佛教音乐除去用木鱼、钟、磬贴上的“佛教标签”外,它的民间味、市俗味实在是太浓了。有一段时间我怀疑中国还有没有真正可以称为佛教音乐的音乐。后来发现,这个观点犯了根本错误。要想判断什么是佛教音乐,首先要对佛教音乐作出比较合理的界定。我曾在《佛教文化》上发表过《佛教音乐的界定》一文,我把一切为佛教所创作、为佛教所利用,于佛教有利,于修行有利的音乐都纳入佛教音乐范畴。这样,你所讲的“一句佛号”以及新创作的佛教民族器乐曲都可以包容进来。这个标准只能放宽,因为如果不放宽,什么是佛教音乐就很难说了。我国佛教和西方宗教不同,他们有虔诚的大音乐家专门为宗教作曲。
田:对。中国就是缺少大音乐家为佛教作曲。我曾经开玩笑地给佛教音乐作了一个非学术性的分类,不科学,但可能符合事实。我认为佛教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弘法的,一类是挣钱的。
凌:其实这两类很难分开。这和坐禅不同,佛教音乐可以一边弘法一边挣钱。做一次音乐佛事,至少有红包供养。
田:的确不好截然分类。据说动物学分类最科学,其实也不尽然。蝙蝠划为哺乳动物,但它会飞。在“水陆法会”上超度它,不知算陆上跑的还是天上飞的。说到佛教音乐,最本质的应当包含四个字:修行、音乐。先看是不是于修行有利,再看音乐有没有佛教意境。要二者兼备才好。现在有人创作佛教音乐,以为曲调舒缓一点,再加上木鱼、磬这些寺院特有的法器,佛教意境就出来了,怎么会这么简单呢?
凌:创作佛教音乐和欣赏佛教音乐,不同宗教修养和不同艺术修养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你认为一句观音圣号反反复复唱来唱去,很难说算是佛教音乐。但这句圣号为亿万人传唱,无论在寺院里还是在信众家里的电子念佛机上,都无休止的唱着这一句。很多人在这音乐声中自我感觉进入一种清净境地,身心得到净化。他们深信这就是佛教音乐。反之,你认为《东方慧光》大型交响乐,以严谨的乐曲结构、深刻的宗教理解,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营造出一幅佛教理想画卷,它的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应当说是“一句圣号”所无法比拟的。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佛教徒都不大认可这就是佛教音乐,因为这与他们心目中的佛教音乐相去太远了。这存在一个层次问题。
田:是存在层次问题。我觉得当务之急仍然是把古代保留下来的传统佛教音乐,如殿堂唱诵、智化寺音乐、五台山音乐、拉卜楞寺音乐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些传统佛乐继承好,保护好。这是我国佛教音乐的主体和基础。二十多年来,我们都做了不少这方面工作,但还远远不够。五台山就因为缺少资金而陷入困境。
凌:智化寺音乐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培养出的新一代传人跑得差不多了。用现代手段可以保存音乐和各种资料,但以传统的传承形式继续流传就太困难了。不过一些本非佛教艺术精华而市俗化又太严重的内容保留的意义也不太大。当然,从民俗学角度来保留这些文化则又当别论。
田:说到佛教音乐中的器乐曲市俗化问题,这是和佛教从宋元到明清市俗化演变相一致的。佛教世俗化,带动了相关艺术市俗化。
凌:寺院文化市俗化不仅从宋元开始,唐代就登峰造极了。当时的寺院里歌舞、戏曲、杂技、曲艺什么都有,简直成了俱乐部。相比而言,现在的佛寺倒清净了许多。
田:你刚才说寺院里有些看似是佛教传统的东西,其实不是佛教的正统,的确有这种情况。我曾经和朴老说,从西藏开始,青海、甘肃、内蒙古、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这大半个圈范围内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唱诵上,都采用雄浑、厚重的共鸣声,也就是我们称为“海潮音”的发声方法。其实这应当是“声明”的余续。西方人惊异一个喉咙竟然能同时发出两个音,认为太了不起了。这是他们不了解佛教声明的缘故。遗憾的是我国的汉传佛教却完全没有继承这一传统。
凌:在《高僧传》里有很多描述唱诵圣手的文字。那声音之雄壮、嘹亮、清越、高昂,必定来自丹田:,也必定受过佛教声明训练。现在用鼻腔和唇齿发声的汉僧的唱诵特点和古籍所记述的唱诵特点相去甚远,似乎无任何渊源可寻。
田:不错。《高僧传》说,那声音可振颤门窗,远播数十里。显然,当时我国的汉传佛教还保持着佛教声明的一些传统。但为什么后来日本列岛、朝鲜半岛这些汉传佛教传播地和藏传佛教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而惟独中国本土的汉传佛教却丢失了这一传统呢?我的研究结果是,宋元以来,江浙一带佛教经忏兴盛,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接触很多,有时甚至在同一场合各行其是。佛教唱诵难免受到戏曲唱腔影响,特别是受到昆曲假嗓的影响,雄厚的“海潮音”就渐渐演变成了今天这种唱法。
凌:你这一看法很有道理。过去我只注意到流行于佛教的曲牌几乎全部来自南北曲,现在看来在声腔方面,佛教也深受戏曲影响。如果想溯本清源,恢复佛教声明的本来特色,恐怕是很困难了。因为用鼻腔和唇齿发音既不需技巧,更不费力,可以轻松应付日日夜夜永无休止的经忏活动。对于佛教音乐,我们不能总停留在继承遗产方面。应当支持有佛教信仰的音乐家进行佛教音乐创作。台湾的佛教音乐创作比较繁荣,你我访台时都有亲身感受。日本在佛教音乐创作上也不落后。日本净土宗首脑滕堂恭俊先生曾送给我不少佛教歌曲集,其中有些是佛教儿歌,写得很有意思。今年初我去泰国和尼泊尔,又收集到一些佛教音乐磁带。在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处还买了一些印度的佛教音乐,那些音乐听起来都很有佛教意境。近年,我在参与策划出版了几种佛教音乐磁带,虽不见得怎么好,但那的的确确是为佛教而创作的歌曲。你是佛教音乐权威,希望你多关心一下佛教音乐的创作。
田:凡是发心创作佛教音乐的,我都大力支持,一般只说好,不说坏。
凌:刚才我们说到传统佛教音乐和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关系极为密切,就佛教音乐而言,它不为宗教原创这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但寺院是一个保留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与世隔绝或半隔绝、世代相传的延续性,寺院财产的集体所有,是决定这一点的原因。例如智化寺音乐就是以一种极保守的方式在寺院里流传了五百多年,这些古代音乐得以再现今天,就继承传统音乐来讲,这是不是一件幸事呢?
田:当然是一件幸事。多年流传在寺院里的器乐曲,本来就是我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还以智化寺音乐为例谈谈这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国着名音乐学家杨荫浏和查阜西等人对智化寺音乐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考察中,杨先生对智化寺音乐的“历史与音乐传统”、“艺僧情况”、“曲调”、“乐谱”、“宫调”、“乐器”、“音律矛盾及解决途径”、“绝对音高”、“曲牌名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历史和音乐形态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他指出,智化寺艺僧所有之笙有十七簧,是北宋“大乐”笙的旧制。智化寺艺僧所用之管为九孔,对照陈《乐书》记载,这确是北宋教坊的遗制。这些考察,在音乐学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这也不能不归功于艺僧以宗教的形式忠实的保存了古代民间音乐,使今人可以通过这些音乐“活化石”探索古代音乐的来龙去脉。
凌:研究古代佛教音乐可以发现很多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宝贵遗产。从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入手,同样可以了解古代佛教音乐的渊源、演变、发展、分布等一系列问题。1979年开始进行的音乐集成工作,对梳理佛教音乐的脉络应当说作用非常大。
田:四大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新长城”,是我国文化系统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文化收集和整理工程。当中国北方(从东北到华北、西北)各省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陆续编辑完成并陆续出版之后,我们发现智化寺音乐不是孤立的,不是独一无二与其他地区民族民间音乐隔绝的文化现象和艺术品种,也不是惟一保存了古代音乐文化,目前仍然使用着古老的乐器和乐律的音乐形式。它是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北方广大农村并在当地农民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北方笙管乐的一个支系;它是五台山佛乐、晋北道乐、山西八大套、西安鼓乐、河北各地的“音乐会”,东北三省的鼓吹乐血肉相联并同属于一个元体系。它们不但有着大致相同的乐器、乐律、风格和演奏方式,也有许多共同拥有的乐曲和传承方式。
凌:1986年我们冲破重重障碍,策划了北京佛教音乐团赴德国、法国、瑞士演出,这是中国古老的宗教音乐第一次走出国门。此后不仅智化寺音乐多次出国演出,经你策划,五台山佛乐、拉卜楞寺佛乐也陆续走向世界。
田:那个把民歌的原始音乐和乐器的测音报告都当成“国家机密”的时代永远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世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也持有相同观”。一些热爱中国传统音乐的外国音乐家已经不满足通过我们出国演出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而是希望亲自来中国进行深入研究。我介绍你认识的英国音乐家钟思第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在英中文化协会资助下,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合作对华北的笙管乐进行了较详尽、认真的普查,写出了《中国民间乐社》这一学术论文。这篇学术着作填补了欧洲汉学和音乐学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空白,堪称“开山之作”。总之,包括佛教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走向世界,是对世界音乐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凌:中国的历史太悠久,地域太广阔,民族又太众多。就拿佛教来说,还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之区别,若要细分各宗派,就更复杂了。因此很多乐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搅在一起难解难分。
田:我常用“瞎子摸象”这一佛教寓言来比喻中国音乐学家探索中国传统音乐这一“巨象”的全貌,如今摸了几十年,总算摸清了大致轮廓。但是“瞎子摸象”的故事却没有完全结束,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一部用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全面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专着问世,也还没有一个音乐学家把中国北方这个庞大的笙管乐系统梳理清楚。虽然几乎所有民间“音乐会”的口碑资料都将其传承联系到佛乐、道乐,但中国的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横亘在整个中国北方的“巨象”的共同祖先究竟在那里?既使对智化寺音乐,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比如智化寺音乐本身的来源问题。迄今为止,除了猜测以外,还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目前所谓王振把宫廷音乐带到了智化寺的说法,也更难想象这个太监的家庙便是几乎所有中国北方农村都有的民间笙管乐的共同的渊源。中国音乐学家们的任务是繁重的,仅仅将这些有着紧密关系和许多共同之处的“支乐种”放到一起进行一下比较研究,便是一个极大的工程:智化寺音乐与冀中笙管乐;冀中笙管乐与“山西八大套”;“山西八大套”与“西安乐鼓”……也许,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音乐学会因为这些深入的比较研究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凌:但愿如此。
上一篇: 佛教梵呗学习方法
下一篇: 梵呗与佛教音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