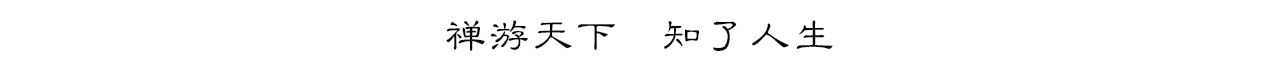鸡足山的沉思 — 我的印度朝圣之旅(九)
按:佛历2560年,西历2016年3月29日,菩萨戒弟子李建偕同老伴,参加广州“蝉友圈·佛旅网”组织的印度朝圣团,一行13人从广州出发,踏上了朝圣之旅的行程,西行万里,历时15天。
[toggle title=”印度朝圣 佛弟子一生的向往” state=”open”]
走近佛子心灵的故乡—印度朝圣散记 2016.3.29
祇园精舍的思念(二)
神圣的蓝毗尼园(三)
拘尸那罗的伤感 (四)
阿难陀舍利塔结缘记(五)
灵鹫山的回忆 (六)
追忆那烂陀(七)
让人难以忘怀的菩提伽耶 (八)
鸡足山的沉思(九)
仙人住处鹿野苑 (十)
恒河岸,生与死同在 (十一)
结语:印度尼泊尔朝圣之旅的几点感悟(十二)
泰姬陵、红城堡的记忆 (外传)
诗歌集·喜贺印度朝圣圆满 (外传)
[/toggle]

这是我们在印度朝圣起的最早的一天,4:30早餐,5:20出发去朝圣鸡足山,是我们行程中的第12天。
印度鸡足山,位于比哈尔邦,因其山顶三峰状似鸡足而得名。根据佛经记载,禅宗初祖迦叶尊者在这里入定,受佛陀嘱托,等待未来弥勒佛于56亿年后降生成佛,将佛陀衣钵传给弥勒佛,因而在佛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高峦陗无极,深壑洞无涯。山麓溪涧,乔林罗谷。冈岑岭嶂,繁草被岩。峻起三峰,傍挺绝崿……其后尊者大迦叶波居中寂灭,不敢指言,故云尊足。”
迦叶尊者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为佛陀弟子中最无执着之念者。人格清廉,深受佛陀信赖,于佛弟子中曾受佛陀分予半座。佛陀入灭后,成为教团之统率者,于王舍城召集第一次经典结集。禅宗以其为佛弟子中修无执着行之第一人,特尊为头陀第一。又以“拈花微笑”之故事,至今传诵不绝。所以到此山朝礼,意义非凡。
从菩提伽耶出发大约50公里的路程,我们却走了约两个小时。因为整个路程都是乡间小道,车速只能开20公里。领队小徐说,大多数去印度朝圣的人,没能到此,觉得十分遗憾。因为这里地处偏僻的山区,多数朝圣者不知道它在哪,印度当地人也很少知道。更因为山路的崎岖难行而放弃。这条线路是蝉友圈·佛旅网遵循“以护持四众朝圣游学,接引大众亲近正法”的宗旨,历经千难万险开辟出来的朝圣线路,对于每一个佛弟子来说此行相当殊胜。
车行约两个小时后,到达一个小镇停车,开始徒步而上,跨过铁路再经过一片长满灌木荆棘的树林子后才到达山脚下。我们的身后跟着一群当地村子里的小孩,小的三四岁,大的七八岁,黑瘦单薄,就像在几乎所有的景点见到的一样,紧跟着你,口中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圣号,让人不敢直视那一双天真的眼睛。领队在车上时就对我们说:如果给了他们钱,可能就会害了他,让他觉得这样子还能挣到钱,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或者以此养家糊口,于是就会荒废学业,乃至以游手好闲。再有,如果你给了这个,而没有给其他的,就会引起他们之间的嫉恨和打架,引起他们的烦恼,这都是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建议我们不要打开钱包。这话当然是对的,不是我们没有慈悲心,心疼自己的钱,实在是怕毁了他们。
到山根时,小孩子不走了,可能觉得上山很累。这时又上来一伙十六七岁的大孩子,磨蹭在每个人的身边,要替你背包,要搀扶着你。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老者和女性团员,几乎就要架着你往前走。听领队的安排,我们把一些重包让他们背着,下山时再给钱时,让他们觉得这是劳动所得。包可以背,但不会让小伙子搀扶,因为我们就是来体验辛苦的,而不是来享受的。老伴六十多岁了,上山时有点心急,加上天气热,到半山腰时,体力不支觉得很累。我们就走走歇歇,喝点水,继续上山。让我感动的是,领队小徐始终跟着我俩走在最后,这不就是菩萨不舍众生的大爱精神吗!
快到山顶时,经过一座峻峭山崖处,这里的大岩石,仿佛被刀刃切开似的,齐刷刷的一条石缝把巨石分开,从底下往上看去,最大宽度不到两尺,沿着石缝中的石阶往上走,里面黑暗阴沉,领队连忙为我们打开手机照明。传说这是当年已一百二十岁的大迦叶尊者用力攀爬上山,由于岩石挡道非常陡峭,对他老人家来说实在非常费力,于是他就显神通,将手边的柱杖轻轻一划,石头顿时轰然而裂,让出一条小道,让他可以顺利上山,也方便后世的行人。
山顶上,两块巨石的缝隙之间,有着半间屋子大的一方空地上立着大迦叶尊者的神龛,高约三米,内塑尊者金像,我们就此礼拜上香献哈达,并诵《金刚经》一部。
爬山用了两个小时,这时站在山顶,极目眺望,视野开阔,心旷神怡。雾色朦胧的群山、山脚下错落的村舍、田野间一簇簇的绿树和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尽收眼底。我们围坐在尊者像前,享受着凉风的吹拂,法乐充满。据传阿阇世王听到大迦叶入灭的消息,曾来此瞻仰尊者遗容,看见尊者在山中端然入定,庄严无比。我们今天来朝礼,可否见到他老人家?答案是,我们见到了,每一个到此朝礼的人都能见到,那不就是神龛中的尊者金色之身吗!
下山走到那一片绿树婆娑的灌木林时,又看到了守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孩子们。还是一样的热情,一样的紧追不舍。这时,我看到了直到现在还定格在脑中的一幕:七八个七八岁的孩子,一溜蹲在路旁,赤裸的臂膀、脸膛和腿脚上满涂着一层黑泥,朝着我们这些异国的游人憨笑。原本我是想拿出相机,把他们的顽皮留在我的影册中,但经过他们身边时,打消了这个念头,急匆匆的从他们身旁走掉了——我为看到的这一幕心痛,不忍心再拿出相机。在那样毒的太阳底下,我们一个个打着伞,戴着帽子,手里拿着解渴的矿泉水还觉得酷热。而孩子们,没有这些,也没有躲在树底下的荫凉里,这是在玩耍?还是故意取闹,以博得异乡人的同情而得到更多的赏钱?抑或是把他们心底的一种什么情绪表达给我们看呢?

在印度,这样类似的场景已见过很多,每次见到,都会让人的心中五味杂陈,不知所措。笔者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八岁时正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水平最差的年代,也经历过每天家里要打发一个个要饭者的事情。童年的这些窘迫困顿已经被尘封在记忆的最底层,不愿意再想起它,更不愿意再看到它。我曾对队友说:在印度最让人难受、难办的不是酷热的天气和朝圣路上的艰辛,而是打发这些个孩子们。今天在印度,看到的这些孩子,勾起了我记忆里辛酸的一页,一处最敏感的神经。
走不多远,我和老伴把身上的余钱都掏出来,一一的发给这些孩子。
呜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共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家家都有好茶饭,芸芸众生无饥寒!(文章连载中…)